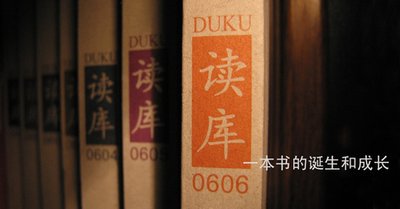
《读库》有一期第一篇就是邓安庆的回乡记,用日记形式记录了过年数天时间,从北京回到湖北乡村老家的情形,冷静的记述了老家的种种生活常态,比如借钱盖屋,年关上门要债,过年去亲友家拜年,留守的老人与长年漂泊在外的子女的沟通,经济窘迫的人们如何挣扎着生活,在一些细节上体现关怀。特别是谈婚论嫁,似乎老大青年无法回避的话题,没有对象的催着找,有对象的催着结婚,结婚的催着生孩子,似乎这样的生活就圆满了,就是等孩子长大再结婚生子,一辈子就算有交代了。每天按部就班的工作、生活,偶尔和朋友喝喝酒聊聊天,这样的生活没什么不好,但这样的生活总是少了一些什么,他是想冒险,尝试不一样的东西。
邓安庆还有一篇文章叫做小说的内心是海洋,写小说其实是窥探欲的满足,当然窥探的不是表面意义上的人的隐私,而是人在复杂的环境中变幻出的最本质的东西,这种东西平时被压抑着,被掩盖着,甚至那个人自己都发现不了,没有特殊情况的出现,他在日常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,被周围人所带来的尊敬包围着,就这样过着平静而又幸福的一生。但是,一旦出现了一个变量,打乱了他的日常生活,就会有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出现。就像《老人与海》中,表面上看是歌颂硬汉精神,其实展示的是老人的另一面。老人日常的生活是打鱼,打不到鱼,就受到周围人的质疑、嘲笑,为此他到远海区,试图找回那些让他荣耀的元素。大鱼就是内心的满足。但真实的情况似乎不是这样的。没有进入他的内心,就永远发现不了。就像技术精准的垂钓者会根据浮在水上的鱼漂来判断鱼是否上钩,有多大,大概是什么类型的。边上的看客就只能看见平静的水面,看不到鱼面对鱼饵诱惑时内心的挣扎,面对被钩住时身体的挣扎和被甩到鱼篓里时绝望的呼吸。
邓安庆的回乡记中遭遇了催婚这样的头疼又难以避免的事情,在他集结成书的《山中的糖果》、《柔软的距离》中仍然会有这样的情况,他也都或明或暗的进行了解释。他最近出的中短篇小说集《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》显示了技巧的成熟与拓展。但是他的小说与记述不是截然分开的。因为小说是虚构的,这是人尽皆知的道理,但是,小说允许虚构,小说中的元素却不能虚构,即使是最畅销的穿越、探秘类小说,依然有作者的背景元素。纯粹虚构,和生活没有关系的小说是写不出来的,写出来的也是胡编乱造。而在读一些小说时,会让人很难过,那种干巴巴的语言,程式化的情节,人物造型的淡薄,一阵风就可以刮走,居然还长篇大论的写,写了一部又一部,让读者的兴趣从浓到淡,甚至坚持读完的兴趣都没有。好的小说是常读常新的,它既离不开所处的社会,又要超越所处的社会,在保持一定的距离中审视当下的生活,这些都是真实的基础。没有真实,小说就没有生命。
在当今的社会中,各种离奇的故事都会发生,各种神奇的情节都会出现,事物变化的程度远远超过小说家小说中所展现的内容,仅仅是罗列怪异的记述,都可以扣人心弦,但小说并不是故事会,不是单单靠离奇玄幻的情节取胜的,而是有背后的内容。在一段段看似平常,看似简单、看似平淡的文字中隐藏着那个时代对于人的最大的智慧,思考。邓安庆的小说,杂记,俯身在卑微的尘土中,写的是身边人的故事,既有烟火气,又充沛着生命的元气,这样好看的文字实不多见,他在写完《我认识了一个索马里海盗》后说,“这本书陆陆续续写了三四年,时常有焦虑不安和自我怀疑之时,但每逢奇妙时刻,都深感创作能得到的愉悦感是如此之大,能写出来真是非常大的幸福。”







